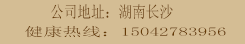鍖椾含涓鐧界櫆椋庡尰闄㈠钩瀹夊尰闄? http://m.39.net/baidianfeng/a_8408165.html年,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相继失去其“哈里发国”和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国际反恐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然而,新冠疫情肆虐以来,“伊斯兰国”将全球危险转变为地区机会,利用国际社会集中精力应对疫情之机伺机反扑,谋求复苏迹象明显。“基地”组织也转变战略、积聚实力、伺机而动。美、德等发达国家相继爆发白人至上恐怖袭击,西方极右恐怖势力再次泛滥。新冠病毒蔓延迫使各国将抗击疫情作为首要任务,反恐优先地位进一步下降。大国参与国际反恐意愿降低,弱小国家反恐能力举措又乏善可陈。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反恐和去极端化面临新挑战。国际社会应保持警钟长鸣,注重预先防范,力争把恐怖主义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坚持重拳出击,加强网络治理,严防网络空间成为恐怖主义肆虐的新阵地;弘扬多边主义,深化国际合作,齐心协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当前,恐怖主义依然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现实威胁。据不完全统计,年全球恐怖袭击近起,导致至少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名受害者和名袭击者[1]。年以来,“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极右恐怖势力纷纷利用各国政策调整形成的真空,借疫情引发的混乱和恐惧散播仇恨,在宣传与招募力度上不断“加码”,反复敦促追随者策动恐怖袭击,甚至将新冠病毒作为生物武器[2]。当前,各国普遍将应对疫情作为当务之急,国际反恐失去优先地位。因此,有必要对新形势下国际反恐面临的挑战及因应之策进行探究,以明确努力方向和目标。一、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持续上升年以来,以“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为“领头羊”的国际恐怖势力仍在全球肆虐。“伊斯兰国”将疫情视为削弱“敌人”、提升影响的良机,谋求卷土重来。“基地”组织利用“伊斯兰国”溃败之机伺图夺取全球“圣战”的主导权。与此同时,极右恐怖势力迅速抬头,对欧美等西方国家威胁呈不断上升态势。(一)“伊斯兰国”借“疫”生乱当前,“伊斯兰国”是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主要祸根。其不仅掌握1亿美元恐怖资金,还有1万多名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叙利亚“大本营”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将矛头对准安全部队与政府目标,不断发动“消耗战”与“游击战”,阻碍政府进行有效的安全治理,迟滞伊叙新秩序的建立,旨在削弱对手的力量。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约有兵力1万人,其中多名武装分子致力于在该国不同地区构建“死亡三角”[4]。年以来,该组织利用疫情和政治动荡造成的安全漏洞,重新在农村地区发动叛乱,并试图在伊东北部哈姆林山脉建立“安全区”。其对伊袭击主要集中在迪亚拉、基尔库克、安巴尔、萨拉赫丁等省。在叙利亚,“伊斯兰国”主要攻击能源设施和军事车队,并设立检查站实施暗杀。其对叙袭击集中在代尔祖尔、拉卡、霍姆斯、哈塞克等省。近日,“伊斯兰国”宣称年在伊策动起恐怖袭击[5],在叙策动59起恐怖袭击[6],袭击次数比年大幅提升。不仅在中东,“伊斯兰国”及其分支机构在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活动也很猖獗。在南亚,美塔和平协议签署后,“伊斯兰国”进军南亚途中少了“拦路虎”,其南亚分支“呼罗珊省”(拥有兵力约名)在阿富汗频繁实施高调袭击,并试图吸引反对美塔和平协议的人员,还与“巴塔”(1)1呈现联合趋势,恐怖威胁进一步凸显。在东南亚,“伊斯兰国”利用疫情展开强烈攻势,不仅在菲律宾受封锁影响严重的贫困农村地区招募“圣战”分子,与政府冲突不断;还企图利用印尼安全机构注意力分散之机策动自杀式恐怖袭击[7]。在非洲,“伊斯兰国”巩固分支机构、策动恐怖袭击、不断占据“领土”、扩大势力范围,试图在十几个国家打造一个新“哈里发国”。其重要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拥有兵力约名)(2)2不断坐大,甚至在控制区域招募成员、掌控贸易、征收税款乃至划分牧场,俨然取代了地方政府的职能[8]。“博科圣地”年月策动了乍得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导致约98名士兵死亡;11月底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报复性杀害名农民。“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GS)与“基地”组织分支“支持伊斯兰教与穆斯林”(JNIM)在萨赫勒地区激烈对抗并争夺地盘。“伊斯兰国”中非分支“伊斯兰国中非省”(ISCAP)年4月开始“崭露头角”,先后袭击刚果(金)与莫桑比克,年8月还攻占莫桑比克北部港口城市滨海莫辛布瓦[9]。在中亚,近一年来,各国面临网络恐怖主义、阿富汗安全威胁以及外籍“圣战”分子回流等问题。疫情期间,“伊斯兰国”采取系列行动:一是宣扬疫情是“真主对西方的惩罚”,值得庆祝。二是敦促追随者在“敌人”因疫情被削弱时发动袭击,采取各种措施消灭“异教徒”和“不信者”[10]。三是试图将病毒武器化。年7月,“伊斯兰国”呼吁印度穆斯林将新冠病毒传播给印度人[11]。四是连番采取“破墙行动”,突袭叙利亚、阿富汗的监狱并释放被关押囚犯。年8月2日,“呼罗珊省”突袭阿富汗贾拉拉巴德东部一所监狱,与阿安全部队交火持续20小时,造成至少9人丧生(包括袭击者),近名囚犯越狱[12]。五是为防止感染疫情,规定保持社交距离,并于年月下旬建议成员不要前往欧洲。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国”在疫情期间数次提及中国。年1月,其媒体“纳巴”(AlNaba)报道称,“一种新病毒正在中国传播死亡与恐惧”。支持“伊斯兰国”的古莱什媒体(QurayshMedia)制作海报声称,“中国:冠状病毒,我们承诺不会忘记”。印尼效忠“伊斯兰国”的本土恐怖组织“神权游击队”还借疫情将中国作为其新的袭击目标[1]。(二)“基地”组织“蓄势待发”年1月,联合国报告指出,“基地”组织仍然具有复原力,威胁日益上升;其附属机构在许多冲突地区,特别是萨赫勒、索马里、也门和叙利亚东北部,比“伊斯兰国”更强大[14]。事实上,过去6年,“伊斯兰国”占据“圣战”活动舞台、吸引国际反恐力量的同时,“基地”组织则趁机悄然重建。这种务实的地方主义战略在叙利亚运作方式中最为明显,活跃在叙伊德利卜地区的“基地”分支“沙姆解放组织”(HTS,曾用名“努斯拉阵线”)聚焦地方事务,注重提供“高效和廉洁治理”,意图建立广泛“公信力”。疫情期间,“沙姆解放组织”借机强化自身作为“合法政府机构”的资格,如发布命令限制集会,并向公众发布抗疫信息等[15]。与“伊斯兰国”残暴、血腥的“建国”路相比,“基地”组织更加深思熟虑,致力于采取隐蔽、秘密、悄然复兴的战略,旨在国际恐怖活动中重塑中心地位。当前,“基地”组织在阿富汗12个省非常活跃,战斗人数介于人至人之间,领导层与“哈卡尼网络”保持着密切联系,现任头目扎瓦希里(Al-Zawahiri)藏匿在阿东北部。扎瓦希里曾于年2月会见“哈卡尼网络”高级头目叶海亚·哈卡尼(YahyaHaqqani),讨论合作事宜[10]。“基地”组织还与阿富汗塔利班(简称“阿塔”)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南部赫尔曼德省省长亚辛·汗(YasinKhan)指出,“基地”组织在阿巴交界的杜兰线以及阿伊(伊朗)边界地带的足迹不断扩大;其在赫尔曼德省迪沙地区有势力存在,并向“阿塔”提供培训和支持。他强调,“阿塔”不可能与“基地”组织及其他外籍“圣战”分子切断联系[16]。“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活跃的同时,还致力于构建全球“圣战”版图。据多家智库评估,“基地”组织拥兵4万人,在全球有20多个分支或同盟组织,其中“沙姆解放组织”2万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人、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b)0人、“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AQIS)0人。其中,索马里“青年党”未受到疫情影响,策动的袭击有增无减,并在控制区抵制政府因疫情采取的隔离措施[10]。“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近一年多来非常活跃,连续策动多起恐怖袭击。年12月6日,21岁的沙特皇家空军防卫部队中尉穆罕默德·阿尔沙姆拉尼(MohammedAlshamrani)在美佛罗里达彭萨科拉海军基地策动枪击案,致使名海军死亡、8人受伤,当时他正在该基地接受航空训练。调查发现,阿尔沙姆拉尼受“基地”组织“理论家”安瓦尔·奥拉基(Anwaral-Awlaki)的教义影响,年变得激进化。袭击当天曾与“基地”负责媒体和互联网招募的阿卜杜拉·马利基直接联系[10]。疫情蔓延后,“基地”组织针对西方民众发布了一份题为《前路:新冠疫情箴言》的声明,宣扬疫情是真主手下“无形的士兵”,强调疫情对美经济造成的损失,宣称疫情“暴露了美国主导下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教唆西方民众转而皈依穆斯林[2]。年7月,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遇害2个月后,“基地”组织在其杂志《一个乌玛》(OneUmmah)发布长达8页的文章,强调西方警察的暴力行为[17]。自该事件导致席卷美国和全球抗议活动开始,“基地”组织针对被边缘化的西方青年发起系统的网络渗透工作,旨在拉拢、招募更多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组织仍向“东伊运”提供人员培训、资金支持及武器装备等。年7月,联合国报告显示,“东伊运”目前有0名至名作战人员,大多部署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的吉斯尔舒古尔地区。该组织在“沙姆解放组织”的保护下与其他武装团体联合作战,主要使用游击战术,避免与叙利亚政府军直接对抗。近期该组织伤亡惨重,一些作战人员和家属正寻求经土耳其和伊朗前往阿富汗北部省份,加入那里的“东伊运”分支[10]。(三)极右恐怖主义威胁急剧上升近年来,右翼恐怖的幽灵再次浮现。美欧及大洋洲等国白人至上恐怖袭击进入多发期,逐渐成为困扰西方国家的“明患”。年新西兰基督城爆发的“·15”案震惊世人,极右恐怖分子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Tarrant)持枪横扫清真寺,导致51人死亡。年10月9日(犹太教赎罪日),德国极右恐怖分子试图闯入犹太教堂作案未遂后,在教堂附近开枪打死2人、打伤2人。他效仿新西兰“·15”案凶手的做法,使用头盔摄像头录制袭击过程并发到网上鼓舞“后继者”。年2月,德国小城哈瑙爆发恐怖袭击,极右恐怖分子托比亚斯·拉特金(TobiasRathjen)持枪袭击水烟吧,导致11人死亡[18]。系列事件意味着西方极右恐怖势力已泛滥到一个新高度。年以来,极右恐怖势力在北美、西欧和大洋洲等西方国家策动袭击的次数激增%,致死人数增加%[19]。年10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年度威胁报告评估称,美面临的最大恐怖主义威胁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独狼’和小团体,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美最持久和致命的威胁”。年和年美极右恐怖袭击占比均达到2/[20]。德国年2月将极右恐怖主义列为该国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21]。英国极右恐怖主义威胁正以惊人速度增长,未来几年将持续威胁英国国家安全[22]。此外,美、德、澳、加、俄等国极右恐怖分子还相互勾结,通过互联网共享宣传、招募、筹资和训练经验,并到彼此国家参加活动,互为支持。年以来,极右恐怖势力将疫情作为传播仇恨的沃土,积极炮制与疫情相关的阴谋论、煽动种族主义情绪、鼓动成员实施恐怖袭击。极右恐怖分子还在各种加密频道呼吁成员将病毒用作生物武器,传播给执法人员和非白人[2]。年月,美国6岁的极右恐怖分子蒂莫西·R·威尔逊(TimothyR.Wilson)企图以医院,后被击毙。二、疫情背景下国际反恐面临新挑战新冠疫情引发世界新变局,也重塑国家安全的优先顺序,给反恐工作带来了若干战略和实际挑战。美国进一步收缩反恐战线,欧洲更加聚焦本土反恐,发展中国家面临防疫与反恐的双重挑战,国际反恐形成合力困难重重。与此同时,隔离措施与互联网的“双刃剑”作用凸显,恐怖势力借机大肆蛊惑宣传,去极端化压力陡增。恐怖势力还谋划利用疫情发动生化恐怖袭击,引发欧美积极
转载请注明:http://www.yemenf.com/ymjj/7781.html
![]() 当前位置: 也门 > 也门简介 > 第期学者观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
当前位置: 也门 > 也门简介 > 第期学者观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
![]() 当前位置: 也门 > 也门简介 > 第期学者观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
当前位置: 也门 > 也门简介 > 第期学者观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