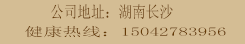![]() 当前位置: 也门 > 也门发展 > 学术观点ldquo一带一路rd
当前位置: 也门 > 也门发展 > 学术观点ldquo一带一路rd

![]() 当前位置: 也门 > 也门发展 > 学术观点ldquo一带一路rd
当前位置: 也门 > 也门发展 > 学术观点ldquo一带一路rd
本文来自 我们今天讨论“一带一路”计划,不得不面对一种从19世纪中期便形成的历史重担。将“一带一路”视为新时期的“马歇尔计划”这类批评,便是这种历史重担的表现。这一历史重担背后,是在殖民与自由主义全球化历史中,以贸易霸权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在这种秩序下,“自由贸易”被当做霸权的旗帜,以一种普遍主义的面貌,执行着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格局所勾勒出的世界图景,是一种帝国式的。它具有高度集中的意志与权力的中心,以及广大的居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在过去的近两个世纪里,这类作为从属的边缘囊括了欧亚内陆、中东、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它们与中心的关系被一系列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的霸权秩序所约束。当然,无论是简单地将反抗视为非理性的“恐怖”,还是将一切暴力行动,均视为反霸权的“革命”均不恰当。
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政治话语中,那些广大的世界霸权秩序的从属地区,被表述为承载了反帝反殖民任务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反抗,在这种政治话语里,被视作在既有的霸权秩序中,对于平等发展权利的追求。这种发展权的平等,超出了“自由贸易”观念中对于规则公平的抽象追求,整合了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发生的具有广泛多样性的反霸权行动,进一步强调了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建立起的国际间关系。这实际上,为“反抗”的行动赋予了超越一族一民边界的历史性意义。
必须承认,贸易作为这种霸权意志的载体,同时又维系了我们这个世界群体之间基本的交流关系。随着这一以互动交通贸易为基础开展的“一带一路”图景,广大的亚洲内陆被联系起来,并从海洋贸易图景下的“边疆”,变为了新的具有广泛可能性的“网络”中的节点。那么,如何理解在“第三世界”观念下的贸易实践,及其背后的平等理想,则是我们今天谈论“一带一路”计划时,所必须整理的历史资源。特别是在处理“一带”问题时,我们深入了亚洲的内陆,并直接面对所谓“政治伊斯兰”的问题。在今天“反恐战争”的格局下,“政治伊斯兰”成为一种需要被治理的不安定因素。而“政治伊斯兰”本身,今天也迅速被暴力对抗行动占领。如何理解,并且回应这种暴力反抗,则是我们今天讨论“一带一路”问题时所必然面对的另一种挑战。本文则希望从这个角度切入,重新从一个统一的历史与政治语境审视“反恐”与“政治伊斯兰”,梳理当代世界中这种“越反恐越恐”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它与中国“一带一路”能否顺利展开,其实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反恐战争”的国际法困境
从年4月8日,巴格达迪宣布叙利亚内战重要反对派军事组织“沙姆地区人民胜利阵线”(,Jabhatan-Nurahli-Ahlial-Shām)[1]开始接受来自所谓“黎凡特与沙姆地区伊斯兰国”(IslamicStateofLevantandal-Sham)的经济支援起至今,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已经从形式上接受了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埃及、索马里等多地的伊斯兰武装圣战组织的认可。在年6月占领伊拉克重镇穆索尔(Mosul)之后,迅速宣布正式成立“哈里发国”(IslamicCaliphate,即所谓的“伊斯兰国”IslamicState)。而在此之前,一些战略报告也指出,ISIS在其控制的叙利亚城市中,已进行了7个多月的“治理行为”(governanceactivities)。[2]这个具有明确政治诉求,有治理行动,有政府结构,以瓦哈比化的伊斯兰教法思想为意识形态,甚至吸引了大量来自海外公民参与战争的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年阿拉伯世界动乱之后,中东及北非地区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而直至年初,在该地区长期进行所谓“反恐战争”行动的美国及欧洲国家,却始终未能提供一种对“伊斯兰国”的政治叙述。而坚持从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出发,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进行维稳式打击的策略所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直至最近《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刊载了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AudreyKurthCronin的长文《ISIS不是一个恐怖组织》。文中称应当将ISIS看作为一个“国家雏形”(pseudo-state)。并且强调,恰是因为美国未能尽早对此做出明确判断,坚持采用传统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恐战略,才导致对ISIS的打击并不奏效。[3]
事实上,即便是在美国最近一次召开的反恐峰会上,奥巴马仍旧将伊斯兰国视为与基地组织一样的恐怖组织(Terroristgroup)。不过,他同时强调,伊斯兰国这类组织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挑战,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暴力极端主义”(Violentextremism),[4]这一概念笼统地将一切“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宣传架构囊括在内,从形式上,构成了一种“自由”对“极端”的意识形态战争。这则讲话从伊斯兰外部视角介入,强调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与伊斯兰信仰本身的区别,并对传统的“文明冲突”话语提出一定程度上的异议。不过,奥巴马同样也强调,“反恐”不仅仅是武力打击,更需要直接与这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争论,把伊斯兰从极端主义话语的绑架下解救出来。与西方媒体与学界经常使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Fundamentalism),或是“政治伊斯兰”(PoliticalIslam)等概念相比,此次讲话中给出的概念淡化了“伊斯兰”因素。
但是,在奥巴马的讲话中,这种意识形态论争的前提条件延续了美国反恐战争以来对伊斯兰问题他者化的视角。除了将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等同为类似的犯罪组织之外,他将两者的意识形态看作并无二致的非理性欺骗性语言。而参与到圣战活动中的青年人,则是受到这种欺骗性语言的蛊惑(deceived),去投奔了这种毫无根基的“幻想”(illusion)。事实上,抛去讲话作为官方政治宣传的因素不谈,这种看法实际上与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以及主流媒体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作为宗教与政治追求的圣战问题他者化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在这种看法下,两者均是世界秩序中破坏和平的非理性暴力。但是,在美国“9·11”;之后备受非议的《爱国法案》前提下,奥巴马这次提出的“暴力极端主义”概念,凸显了作为霸权制度的国家机器与其反对力量之间的对立。与布什时期具有相对明确伊斯兰指向的反恐策略不同,奥巴马这一概念涵盖面更加宽泛。
当前国际社会和平的基础是对现有国际法秩序普遍性的认同。但是,我们同样也必须认识到,今天约束国际间活动的国际法体系,其来源的确是在欧洲基督教国家传统中形成的,以契约关系为前提,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威斯特法利亚结构。虽然,这一国际间行为规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接纳为一般性的准则,并互相以此约束,因此具有实际法律意义上的普遍性。然而,同样也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几乎今天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以及大量中亚穆斯林地区,均经历过漫长的被殖民历史。而今天,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等在内,这些影响此一地区的一系列号召暴力反抗的各类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与圣战组织,则或多或少地将其合法性根植于这种对殖民与帝国主义的痛苦记忆上。[5]今天,建立在这种记忆基础上的暴力对抗意识形态话语随着ISIS的出现,并甚至开始成为建国神话的一部分。这与冷战以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政治变化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具有强烈反西方主义(anti-Westernism)色彩的政治话语形成,其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则来自西方中心的全球国际法秩序对本身殖民历史的策略性淡化,以及自海湾战争以来,西方政治军事霸权在中东地区重新浮现。[6]而自“9·11”之后开始的“反恐战争”(WaronTerror),则更进一步在中东地区加强了这种不平等的现实。
此外,在当代国际法世界秩序框架内,主权国家是作为最重要的国际间行为,特别是战争行为的主体。然而,“反恐战争”却完全超出了这一框架。并将国家对外的战争与政权对内的专政,统一在了一个霸权话语之下。“反恐战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年“9·11”袭击之后,布什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7]而事实上,在当前国际法体系内,对于“正义战争”(justwar)的阐释并无法真正为“反恐战争”提供法理及法律支持。与国际法内一般意义上对战争的定义不同,这一“反恐战争”行动是主权国家(sovereignstate)针对非主权组织(non-stateactor)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除了有传统意义上在国家内进行的针对暴力恐怖犯罪进行的警察行为之外,还包括了派遣正规军前往其他主权国家内进行的追捕及扫荡。可以说,支持“反恐战争”概念的是道义而非法理。而在这一领域内,得以制约战争双方的现代国际战争法缺席,这使得在传统战争中受到法律约束的战俘、战争赔偿、占领地等问题均无法得到有效界定。[8]此外,“恐怖组织”发动的针对另一主权国家进行的暴力行动,能否被视为宣战行为,也存在问题。倘若认可这是一种宣战行为,那么在当前国际法体系中,这类战争行为的责任人则无法确定。进而无从谈起追究战争行为的国家责任(Stateresponsibilities)。虽然在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内,非国家组织的暴力行动通常会被视为是受到国家意志的主使,因而,主权国家仍旧是法律责任体。然而当讨论恐怖主义行为的时候,这一原则产生了局限,即针对某些具有独立建国意识的政治组织,其行为本身无法被法律界定为国家行为(theactofstate),则其组织所在国家的责任就显得非常有限了。[9]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LawCommission)的现有原则,国家是国家责任的唯一主体。[10]因而,仅有在存在法律(dejure)或事实(defacto)代理人行为时,主权国家才能够对非国家组织的“战争”行为产生“国家责任”。[11]
然而,在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正式宣布要求受“恐怖分子影响,并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对这一行为负责,并将“反恐战争”视为保卫人类文明的绝对正义行动。[12]这一文件标志了反恐战争战略中最核心的所谓“布什主义”(BushDoctrine)的正式形成。而这一系统化了的政治话语,接续了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战略,将维护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视为21世纪的主要任务。并将这种在美国单极霸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间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视为人类自由(humanfreedom)与人类尊严(HumanDignity)的唯一保障。而将“恐怖主义”视为对这种世界秩序的根本挑战。[13]
然而,在“布什主义”话语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平等话语被替换为这种有条件的人类自由与尊严。同时,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的“反恐战争”又被视为保障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行为。[14]在这个叙述下,恐怖袭击行动被视为对美式经济与物质繁荣的挑战,而维护世界秩序的平等与人类大同的国际主义目标,被等同于维护美国利益。这就使得原本已经非常模糊的“反恐战争”概念更加面目不清。而随着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开始,“反恐战争”正式扩大为一个主权国家针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的,不受联合国授权制约的军事行动。它甚至以推翻另一个主权国家政府为目标。随后进行的反恐活动,则甚至进一步变成了平叛(counterinsurgent)。甚至,在不少西方战略家眼中,平叛已经成为21世纪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模式。[15]此举则更加凸显了在“反恐战争”背后潜在的国家利益因素,并进一步将无明确国际法实效的“反恐战争”推向了公众、特别是中东和北非阿拉伯穆斯林眼中的侵略战争。[16]一种阿拉伯公众间普遍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仅是希望进一步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并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17]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政治伊斯兰”的诞生,可以说是伊斯兰在19世纪末期被“问题化”的产物。这一概念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对政教分离历史必然性的普遍主义认同。所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一种自我确证的预言:当代“政治伊斯兰”的起源
在今天西方公众视野与政治讨论中对“政治伊斯兰”或者“伊斯兰主义”(Islamism)的兴趣,主要开始于年“9·11”事件之后。可以说,在今天的大众话语中,这两种基本被互换使用的概念,实际上是与“反恐战争”共生的产物。同时,在公共讨论中,“政治伊斯兰”被看做是当代政治现象,基地组织的诞生以及伊朗革命则被视为这种现象的起源,两者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表现。特别是基地组织,其“政治伊斯兰”的地位,直至“9·11”之后才被强调。[18]而在此之前,诞生于冷战时期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背景下的基地组织,其“圣战者”(mujahid)运动则一直在美国“里根主义”(ReganDoctrine)意识形态外交战略中,被叙述成对抗侵略者的“自由斗士”(freedomfighter)。[19]
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英语政治叙述中“政治伊斯兰”的两个属性,即作为“他者化”论述的特性,以及作为身份政治认同的特性。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伊斯兰”价值的判定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并且与其各届政府对于全球战略首要问题的判断密切相关。然而,我们还会发现,从里根主义到小布什的反恐战争话语,均建立在一种绝对的二元逻辑基础上,对于“敌我”关系、“内外”关系展开基本论述。虽然这种二元逻辑构建了对“正义”、“自由”等普世主义关怀的道德叙事,但是,在其背后,仍旧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政治特殊性考量。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构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伪善。这种伪善,不但造成了美国外交,特别是对中东地区外交的短视态势,更进一步滋长了今天中东国家穆斯林中普遍的反美情绪。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政治伊斯兰”的诞生,可以说是伊斯兰在19世纪末期被“问题化”的产物。这一概念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对政教分离历史必然性的普遍主义认同。所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20]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问题时的天然假定。这种建立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历史上的世俗化(Secularisation)观念,成为衡量“好政府”(goodgovernment)的基本标准之一。[21]但是政教分离在欧洲历史语境里诞生于教权与主权的政治性对抗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欧洲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也产生出了管理欧洲教权与主权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一定程度上,政教分离与现代性的关联是在这种欧洲历史特殊性背景中诞生的。然而,这一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经验,却被替换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发展逻辑,成为对“现代化”进程的统一描述。我们假定这场发生在17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事件,可以被作为普遍经验,适用到世界范畴之内。进而假定所有世界的所有宗教,所有的文化,其“现代化”过程必须经历过一个“主权”对抗“教权”,并取得成功的政教分离。倘若没有,那么这种宗教或文化便是非现代的,是中世纪的。
这种建立在二元论逻辑假设基础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也影响到穆斯林学者内部对政治伊斯兰问题的基本理解。但却可以导向与欧美知识分子完全相反的结论。出于论述便利的考虑,这种在穆斯林内部,对伊斯兰在现代语境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讨论,本文将其统一称为“伊斯兰主义”。19世纪末期,一批受到欧洲现代教育的伊斯兰学者开始对穆斯林世界,在欧洲殖民扩张环境下,出现的贫弱现状做出回应。被看作是泛伊斯兰主义鼻祖的阿富汗尼(Jamalal-Dinal-Afghani,-)在其编辑的一份泛伊斯兰主义刊物al-‘Urwaal-wuthqa(《最稳固的联系》)中提出,君主专制实际上有利于实现伊斯兰世界复兴。这是因为,中东穆斯林国家的人们自身修养与教育程度不足以支撑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的民主体制。必须有一位贤能的君主,引导并教育臣民,使之开化。而这种教育所秉承的真知便是传统的伊斯兰思想。[22]在这里体现出的民主与伊斯兰正道之间的二元对立,直至今天还在影响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作为调动模式的伊斯兰主义。[23]
除了阿富汗尼之外,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伊斯兰知识分子中的复兴主义倾向影响深远,表现形式与各自提出的政治方案也各有差异。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Hassanal-Banna,伊斯兰解放党(,即“扎伊布特”)的创始人Taqiuddinal-Nabhani,埃及宗教学者、奥斯曼帝国穆罕穆德·阿里王朝时期曼苏拉(Mansoura)地区的宗教法官(Cadi)AliAbdelRaziq,以及印度改良派伊斯兰学者SayyidAhmadKhan等。虽然这些受到良好西式教育的伊斯兰知识分子统一被看作是影响了“伊斯兰觉醒”(,al-Sahwaal-Islamiyya)运动的核心人物,但是他们之间在回应“西化”挑战时所采用的思想资源与提倡的复兴路径则完全不同。而恰是这种在殖民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从欧洲外部生长起的“复古革命”,构成了当代阿拉伯格局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阿拉伯世界来说,那种强调回到伊斯兰原初的“伊斯兰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实际上恰恰不但是一种现代的产物,更是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
无论是他者化的“政治伊斯兰”还是伊斯兰世界内生的“伊斯兰主义”,均可以被看作是今天世界范围内同一种二元逻辑的一体两面。
事实上,无论是他者化的“政治伊斯兰”还是伊斯兰世界内生的“伊斯兰主义”,均可以被看作是今天世界范围内同一种二元逻辑的一体两面。它们共享了一种假设,即“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壁垒森严的同质化历史。上世纪70年代,摩洛哥学者AbdallahLaroui在其《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危机》(TheCrisisoftheArabIntellectual)一书中谈到了一种笼罩阿拉伯人的身份危机。他认为,阿拉伯人被困在一座思想监狱里:一边是过去的阿拉伯文化,一边是当代的西方文化;选择前者就会被现代抛弃,而选择后者,则会被阿拉伯人的认同所抛弃。这种情况,他称之为“穆斯林的困境”(theMuslimsdilemma)。[24]概括一下,就是说:如果穆斯林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伊斯兰的属性;但是,如果我们维护自己的伊斯兰属性,那我们就会被这个现代社会抛弃。这种将“伊斯兰”与“现代”相对立的二元认识论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例如“原教旨主义者”会强调,之所以今天伊斯兰世界会遭遇如此多的苦难,究其原委,就是因为背离了伊斯兰的正道本源,落入过分“现代”的陷阱的结果。这种二元逻辑在回应伊斯兰世界遭遇的治理危机时显得格外有效。NazihAyubi在其《政治伊斯兰》(PoliticalIslam)一书中便明确指出,那些正在走向现代的国家实际上未能真正提供他们所保证的繁荣与发展。而这种治理与经济的危机则直接导致了伊斯兰主义的兴起。[25]
在阿拉伯学者的讨论中,“伊斯兰主义”本质上是从教法角度,对伊斯兰与现代国家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伊斯兰主义”本身便是穆斯林国家/地区/人群,从19世纪以来开始,对殖民主义全球贸易、两次世界大战、威尔逊主义、冷战意识形态及其国际结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重大全球秩序性问题,结合自身现实做出的理论回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伊斯兰主义”本身便是政治实践的多样性产物。同样,我们也可以将他者化的“政治伊斯兰”看作是一种在欧美主导的“自由贸易”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对冲突的合理化阐释。
英美学界对“政治伊斯兰”他者化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老派的伊斯兰研究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BernardLewis。此人年9月在《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RootsofMuslimRage)的文章。[26]在他看来,伊斯兰与现代世界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而伊斯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其宗教本身的问题。当然,刘易斯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进行类似的讨论。这种文明本质论的提法在亨廷顿身上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论述。从对伊斯兰的讨论,扩展到对全球“文明”的系统性分析。第二类,以GrahamFuller为代表,将政治伊斯兰视为一种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认同。从调动方式上来看,与民族主义、宗族主义这类身份政治认同方式并无太大差异。在富勒看来,政治伊斯兰是阿拉伯世界对全球化与殖民主义的回应。它形成了一种有效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ideologicalforce),承担了阿拉伯世界反抗今天全球化过程中来自西方挑战的任务。[27]其分析基础延续了伯纳德·刘易斯等人的文明观念。
这种以伊斯兰宗教为调动手段的暴力,将自身包装在反殖民与反霸权的口号下。这更进一步契合了西方自19世纪以来对野蛮的东方形成的他者化想象。而伊斯兰的暴力,则更是以其反西方的诉求,构成了一种“自我确证的预言”。
第三类观点代表人物是OlivierRoy与TrevorStanley。他们的观点更为大众媒体所熟悉,也更明确地显示出对“政治伊斯兰”的讨论作为一个西方内部问题的逻辑特性。在他们看来,伊斯兰的本质问题是因为不够“世俗”,没有经过宗教改革。而“政治伊斯兰”本质上是一种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本质差异。奥利威亚·罗伊表示,他对“伊斯兰主义”的讨论,材料均来自于当代伊斯兰主义者的著作,而不考虑其在伊斯兰教法内部的发展脉络。[28]因此,罗伊的提问方式完全将伊斯兰他者化,实际处理的是欧洲内部的“伊斯兰恐慌”(Islamophobia)与穆斯林移民认同问题。在他看来,今天伊斯兰移民与西方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伊斯兰的(前现代)宗教秩序与西方的现代世俗化秩序之间的本质冲突。[29]从欧洲内部出发,伊斯兰主义的反抗还被看成为第三世界与发展中国家、特权阶级与被全球化进程排除在外的人们之间的冲突。[30]罗伊指出,即便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问题意识的产生,从深层次的逻辑假设来看,无疑也是对西方式“政教分离”()历史普遍性的默认。伊斯兰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对当代欧洲内部世俗主义社会生活问题的宗教回应。[31]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转载请注明:http://www.yemenf.com/ymfz/7751.html